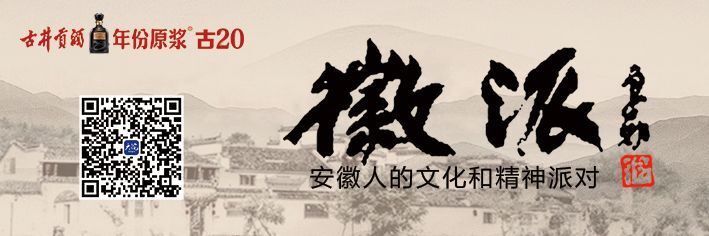
省作协副主席、70后代表作家陈家桥日前做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光明的大皖徽派直播,从自己正在创作的《时代三部曲》切入,陈家桥从作家的童年与故乡、更加开放的时代和创作的自由、一个作家的文化自觉和感受力等方面,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认知。他直言,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要做到“君子慎独”,不能潦草对待,既要能感受到过往如一棵树一片稻田的坚韧生命,也要勇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他提倡更新的语言更新的形式和更新的小说文本,当然,这一切要有根,那个根就是既是归宿也是出发点的故乡。
 作家陈家桥
作家陈家桥
作家需要回答这个时代的提问
徽派:先跟我们聊聊手头上正在创作的《时代三部曲》吧。
陈家桥:《时代三部曲》的三本书之间是有关联的,我个人觉得写作还是要有计划一点,告知公众的一个作品计划,相对作家本人也是一个倒逼。怎么说呢,每个作家创作不同,这个题材对我来说消耗的体力比较大,希望按照既定的计划完成。第一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后面两本明年和后年,虽然是三部曲,每一部的体量也不是很大,更多希望通过三部作品展现百年的变化,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情,书和我自己的乡村经验有很强的关联,写一个和个人密切相关的故事,是一种记忆的生发。
第一本《红星闪闪》讲述一个从六安走出的红军老战士的革命生涯,《波光粼粼》是五六十年代修建淠史杭,很大的一个工程,第三部《蒸蒸日上》就是我这一代人,70后,展现城市和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安徽是农业省份,特别在皖西,客观讲当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用小说的方式把这些记录下来。
徽派:其实之前会觉得,这个三部曲会是一个主旋律和命题作文。但您也说这里面牵扯到一个故乡和童年,而且对您来说是一个体力活。
陈家桥:故乡,以前写作也提到过。人到中年,看事情的视角和心态都平和了很多,包容性更多。这时候再看故乡,视角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说是艺术的真实,是不是一个命题作文,实际上真的不是。人到中年以后会自发观照童年和故乡,还有就是对重大社会现实,整体的一个把握能力都有变化,现代人的生活,城市里的角落,其实都可以选择。但人到中年,会拉动你的知识、审美和艺术观,趋向于对大的记忆和社会脉络进行梳理。感谢这个时代,我们毕竟生活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写作的人有理由也有必要,应该有勇气把这个写出来。这次不同的是,我倾向于从个人化的角度去写个性化的东西,上了一定年龄以后,每个人的写作都是和社会,和主流结合很紧密,你要回答时代的提问,生活变化背后的逻辑,为什么?我还是很乐意去写。而且写的过程中,我的写作的方法和角度,写作带给我的新的体验是一脉相承的,并没有发生巨大的改变。最好的写作是合适你的,自然的,不能强行写你陌生的东西,真实自然流畅是共有的。
徽派:麦家的《人生海海》也说到了童年经验和记忆,它对作家的意义在哪里?
陈家桥:很多人提到童年对作家的重要,童年的经验积累和印象,有些时候并不是发生在实际的客观的逻辑的瞬间,更是发生在一个人的潜意识和经验更丰富的时候,都是童年经验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有时候大家说你很先锋,又说你很城市化,现在又写乡土的东西,有些跳跃是吧。在不同的材料之间,文本上会产生新的东西,我快50岁了,再把童年视角拉回来,和你青春期写作的乡土印象是不同的。有了城市经验和现代性,反过来看乡村,我们承受的对命运改变带来的痛苦、荣誉、幸福、挣扎和融入,整个过程很丰富的。你刚才说到的麦家也是,不同作家在不同阶段都会或多或少写到童年和故乡。
把写作当回事要做到“君子慎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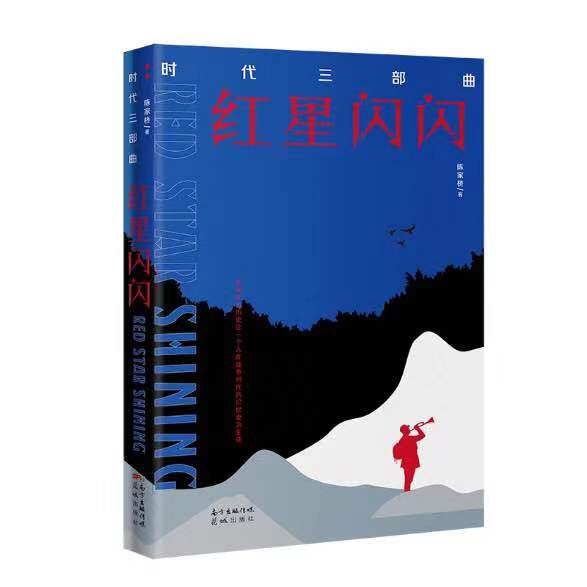 《时代三部曲》第一部
《时代三部曲》第一部
徽派:那你对故乡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三部曲里第一部,好像有外祖父的影子。
陈家桥:《红星闪闪》写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战争经历,这种作品很多。我这样一个作家来写,追求不同的角度,从写作经验上,带给别人的阅读感受上,求新求变。里面有我的外祖父的影子,他当年确实是红军战士,但是很普通的战士。问题就在如何挖掘普通战士的传奇性,突出闪光的东西。我小时候,外祖父有一次放炮仗,他在手上就把炮仗炸了,当时觉得他胆子很大,给我的震动是非常大的。而且我想,因为他生活在六安乡下农村,特别朴实,讲的话,给人的感觉,您不去点他触动他,他永远像一棵树一片稻田,真诚,内敛,朴实,自尊,这些品质在我老家的老年人身上非常普遍,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个村庄的人。今天富足的生活,离不开农村的付出。外祖父是红军,我也是零零散散听到一些。过去的年代,理想道德情操,身上坚韧的东西,是人的底色,对我是非常大的教育。
徽派: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陈家桥:写作和构思的过程中,写小说本身也是自我教育,完善你的人格。作品写得怎么样,读者判断,但作家要有自觉,要知道写作承担的作用,古人说君子慎独,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注重自己的形象和品性,始终有一双眼睛在观照着你。我这次写三部曲不论是主旋律主流写故乡,还是现代性表达,都是在完成,通过写历史过去的事思考提升自己。写作的目的可能有功利心、市场性、带着消费社会的特征,但一个真正把写作当回事的,要认真考虑不能潦草对待的。
徽派:文化的自觉性难能可贵,之前您身上的标签是先锋作家,现在提笔写乡村,这个自觉在找什么。
陈家桥:中国现在是巨变的社会,是开放的,现在注重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又是高度融合的全球化时代。而作家永远面对这种情况,你写出来就是你的故事,作者的印记、思考和观点。第二部关于淠史杭的,正在写,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是带着自己回到那个你还没有出生的时代,1958年淠史杭,最高峰一天80万人在工地上干活,作家虚构但不能脱离现实,不能离谱。我寻找过去的人,真的很感动。渡槽,空中的水管子,在河的上空,在两座山之间架起来,我们那地方人那一代人,叫“扒”渡槽,我说不是架起来么?他们扭转不了这个认识,对他们来说是一样的,都是劳动,举起来还是挖下去,在他们来说都叫扒。冬天穿着草鞋也要去扒,这个强大的动力,为了什么?充满着激情,和自然作斗争,实在因为生活过于艰难和困难,就要付出今天看来极强的体力劳动,再来回首,仍然用这样的词汇,扒。这些人跟你对话的时候,实际上对作家来说,才华重要还是语言重要?更重要是你的感受力,你对这个无动于衷,写得再好又怎么样?不能打动人。
 徽派访谈中
徽派访谈中
徽派:一个作家的感受力是非常重要的。
陈家桥:我写作的时候,回忆起这些人,上了岁数的,很老实很本分,这个是包围在你的周围,促使你热爱写作,写下去觉得有意思的很重要的方面。作家年轻的时候,想出名想成大事业,到中年知道,人的成就和你人本身的综合的处理世界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不需要通过那些花里胡哨的方式讲过去的故事和童年经验。现在中国作家存在问题,始终处在形式上的陈旧——小说的形式,虚构的艺术,还是很陈旧。当你有了感受力,你要有现代性的表达,过去说扒渡槽,怎么表述?树立一个高大全的形象,再树立一个对立面?今天我们再去看,整整一代人为什么去这么做,一代人几代人都处在强大的动力上,把乡土社会改变成现代性社会。小说越来越洋气了,人越来越时髦,你沉入到一个精神层面,几代人完成的是这个,现代化的转型现代性的转型。《波光粼粼》我就想到,两个人的书信往来,书信体,挑战是能不能体现书信往来人的语境,强调里面的内容,我是觉得,固然社会风貌还原很重要,更重要是你今天再现需要掌握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的整体性的原因是什么。一男一女通信,一个在扒河,一个在城里,有没有恋爱的可能性?我越写越觉得,没有,几十封信始终没有要谈恋爱。一个说我扒河很累,女的就说你要继续好好做一个农民吧,有人在那个时代是理性的,有人是感性的,个人的命运和社会之间,是被塑造的。时代的烙印就在于,它就是把你塑造成那样。虽然你不在那个时代,想想是可以代入的。写小说有一个好处,可以学会宽容。我以前塑造过坏的人物,坏的事情,今天来看,社会那么大,艺术总体那么大门类这么多,不管什么东西,最终都会成为一种经验,会过去。
乡土故乡是归宿也是一个出发点
徽派:感觉你老在提人到中年,而且满怀感恩的心。
陈家桥:我很羡慕新的一代小说家,譬如大头马,他们的写作很尖锐很锋利,写出很多新的东西,那本书叫《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反讽啊,不畅销,还教你怎么写。社会越丰富越宽容,整体越大的时候,自由度更高,你更能腾挪。人到中年,潜在的意思,不管你年纪大也好,迫切也好,这些不构成真正的危机,关键是不因为形式的落后产生危机感。我们都是城市里熟悉的陌生人,过去的城也不是现在的城市,有人说合肥可以说是过去十年国际上走得最快的城市之一,困惑在于,这些变化激荡不断压到你身上,是不是还能让你自己通畅顺利。中国文学包括小说,总在某个阶段、时间点面临一个拐点,突然发现小说的美学,故事打动人的点会悄悄发生变化。贾平凹当然还在写,更好的作家更年轻的作家会突然更重要更受欢迎。
 徽派直播中
徽派直播中
徽派:这是您的期待。现在的时代有很大的自由度,您带着70后代表作家的标签,对自己有什么新的思索。
陈家桥:新世纪以来,小说本身来讲,写大故事的在慢慢消解下降,表现形式的网络化,人物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作家和80后不一样,70后还有过去叙事的集合,这一代作家承担着这么一项写作上的责任和面貌——勾连了上一代人,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再过渡到网络写作、市场化写作、国际化写作,几个版块之间过渡作用。70后有可能在未来10年会出相对比较大的作品。我是写的比较多的,所以也会被诟病,写得粗糙。实际上跟每个人写作风格有关系,并不重要,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你想透过写作认知世界,没有大部头作品是困难的。文学绕不开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他们这些人的作品,包括我们的鲁迅和曹雪芹,构成了人类精神谱系大背景,历史在小说中建立的图谱和人物背景,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构筑各种艺术的基础和母体,人想跳开传统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笑话。巨大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是处在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间,作家可以写一些小的东西,也应该有更具有时代感的题材,故乡和乡土,是写作虚构的过程中支撑你的基础,没有童年和经验,你就是生活在城市的普通人,你背后的根和绳子还会断,你会飘。乡土故乡是归宿,也是一个出发点,让你不断往前走,有一个坐标背景,也是参照,一个保障,一个给养,也很重要。
徽派:这么多年您也一直不辍笔,一直爱小说这一块,小说文本对您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陈家桥:很多人写很多,涉猎门类很多,我基本是小说,百分之九十五是小说。纯粹是个人兴趣,就是觉得小说特别有意思。小说本身的题材写法上的追求上的巨大区别,足以满足我的写作。没有文体比小说更好,更能呈现纸上的历史感。当然中国人说诗言志,评论啊都可以,优秀的电影文本也是。但现代社会,没有比小说更能说明生活。读者也好,评论界也好,中国情况就是人很多,厉害的人也很多,好的东西一定会出来的,社会运行非常高效。小说是世俗的,和生活挂得很紧的,越世俗越有智慧,《金瓶梅》《红楼梦》都是世俗生活,但有大智慧在里面。靠近真理,靠近极限,有些人通过道德有些人通过艺术,越回到开放的时代,现代化的社会,越要有道义上的公平。传统认为小说虚头巴脑的,其实不是这样。好的文本当然不止小说,大部头的小说是,好的电影也是,顶尖的音乐也是,莫扎特巴赫,李白杜甫苏轼在那个时代,精美绝伦的意象塑造,也达到他们的顶峰。把握世界认知历史,都要整合起来。好的小说,你采取的形式要新颖一些,小说的有趣有意思有意味远远胜过那些说教,要内置在故事里,外在的形式让人能接受而且自然。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 蒋楠楠/文 薛重廉/摄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