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王阳明生活》一书,方知这位被梁启超誉为“明代第一流人物”的心学大师,在平定宁王之乱后,竟也如陶渊明般写下“辞职信”,七次上书乞求归隐山林。奏疏中“臣病日深,若再驱驰道路,必至颠仆”的恳切之辞,字字皆是宦海沉浮的血泪凝练——既是对功高震主的清醒避让,亦是对“致良知”哲学的躬身实践。
从彭泽县衙解下的官印,到泛舟太湖时荡开的水纹,从岭南瘴雨泼墨处刺破苍茫的几竿青篁,到终南山巅凝结的寒露,历代名士用不同形式的“辞职信”,书写着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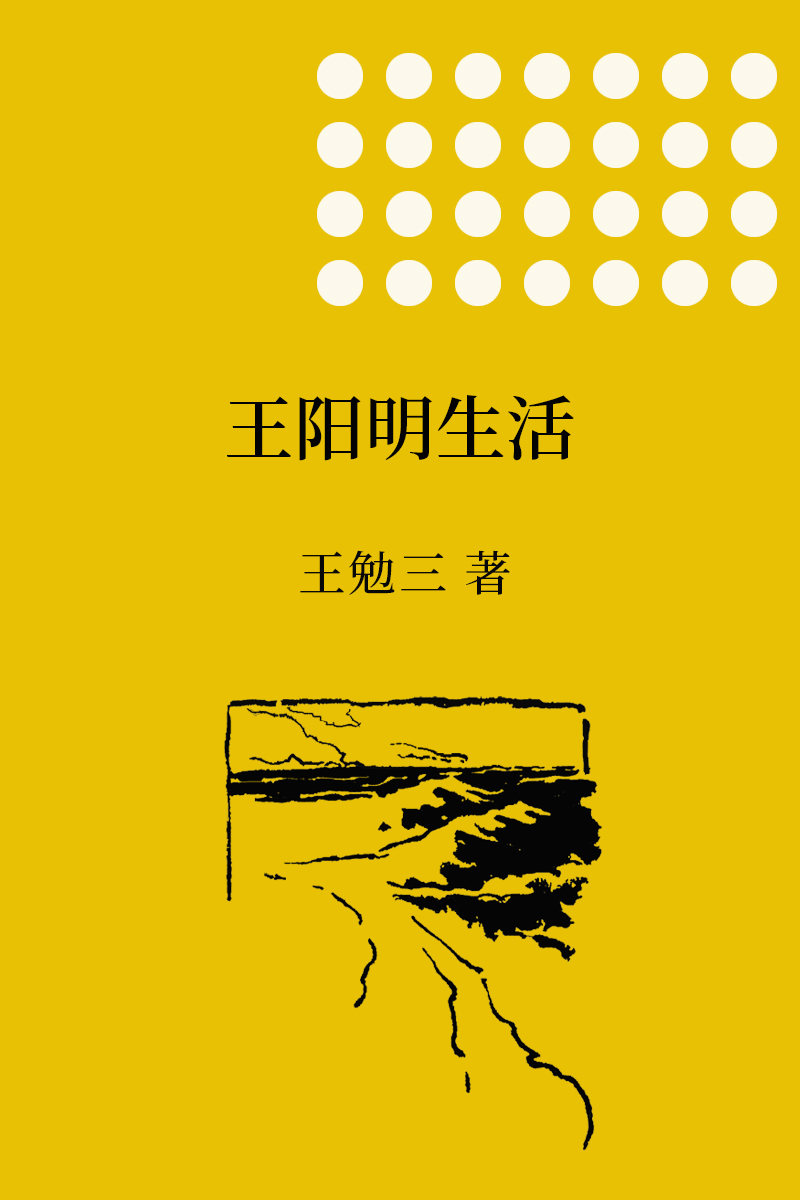
一纸辞章:文人的风骨与尊严
东晋隆安年间,江州彭泽县令陶渊明面对督邮巡查的公文,将官服叠放整齐,留下一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便踏上了归田之路。这场被后世简化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辞职事件,实则是知识分子对体制化生存的彻底反叛。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不仅描绘了山水田园,更构建了“守拙归园田”的精神家园。千年后,敦煌莫高窟第103窟的《陶潜赏菊图》中,诗人衣袂被山风卷起,俯身采菊的瞬间凝固成永恒的挣脱,画壁斑驳处依稀可见“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题记,那抹山岚缭绕的留白,恰似文人心中永不褪色的归隐梦。
而那位在《王阳明生活》中令人唏嘘的哲人,终其一生未能如愿归隐。明正德十四年,王阳明虽平定宁王叛乱,却陷入更凶险的政治漩涡。他在《乞休致疏》中连陈病躯难支之苦:“左肢挛缩,痰嗽交作……恐颠仆道路,死无足惜,但贻君父之忧”,字句如刀,剖开明代文臣“忠孝两难”的集体困境。然而朝廷却以“移孝作忠”之名强令其赴广西平乱,五十六岁的他行至赣粤交界的南安青龙铺,一叶孤舟成为心学巨擘的生命终点。据《南安府志》载,此地旧有“光明亭”遗址,残碑刻“月落舟横野渡空”七字,恰合阳明先生临终情境。而孤舟中的那句绝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至今仍在章水河畔回响。其弟子钱德洪在《王阳明年谱》中痛陈:“使先生得优游林下,尽阐斯道,其所造讵可量哉!”史家钱穆也曾感叹:“若阳明得十年林下光阴,心学体系或更臻圆融。”然历史不容假设——他写于广西瘴疠之地剿匪途中的《答聂文蔚书》,恰是“事上磨练”的终极注脚:心学在此挣脱书斋,化作救治民瘼的良方。那一朵朵散落在山间的野百合记得,那个临终仍念叨“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的身影,早已将光明播洒在知行合一的路上。
去留之间:文明的精神突围
范蠡泛舟太湖的身影,在《越绝书》中化作一道文化分水岭。《越绝内经九术》载其助越王勾践伐吴时,“贵籴粟槁,以空其邦;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以九术耗尽吴国国力,终成霸业。然功成之际,这位“以术亡吴”的谋士却悄然离去,化身“陶朱公”泛舟五湖。临行前致信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越绝书·越绝外传记范伯》)
杭州西湖畔的范公祠里,“忠以为国,智以保身”的楹联下,游人常驻足凝视一尊范蠡的青铜像——但见他左手执算筹计量天下财富,右手持鱼竿垂钓江湖风云,衣摆纹饰间由三枚铜钱串起的《史记》“三致千金三散之”的典故若隐若现。这种“富行其德”的实践,早于西方慈善理念千余年,却在《太平广记》中被演绎为“散财星君”的神话,恰似水波中的倒影,虚实交织间映照出民间对智慧与良知的永恒追慕。而在明代话本《三言二拍》中被演绎为“散财星君点化迷途客”的故事,恰印证了《史记》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范蠡的选择,实为对功利社会的超前解构。
北宋元祐四年,苏轼在汴京官舍写下《乞郡札子》。这位历经乌台诗案磨难的文豪,以“老病日侵”为由自请外放,却在杭州疏浚西湖,于苏堤春晓中获得新生。元祐三年,他在奏疏中直言:“臣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台谏,例为怨仇”,道尽党争漩涡中的无奈。然而正是这种“被迫归隐”,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篇章——贬谪黄州时,他拄着竹杖踏着芒鞋吟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将政治困顿升华为超然境界;流放惠州时,他笑谈“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以旷达笔墨重绘了生命的经纬。元人绘《东坡笠屐图》中,他拄着竹杖踏着芒鞋行走于海南黎寨,身后跟着捧书问学的黎族学子——这是对“进退出处”最生动的诠释:真正的文化传承,从不在庙堂高阁,而在民间阡陌。儋州三年,他结庐桄榔庵,将中原典籍译成黎语,当地至今流传“东坡话”方言,比任何奏章更能注解“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真谛。
 音乐剧《苏东坡》.王彪/摄
音乐剧《苏东坡》.王彪/摄
文化基因:进退中的永恒辩题
陶渊明的菊、王阳明的剑、范蠡的舟、苏轼的竹,共同编织成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腾。张衡在《归田赋》中“仰飞纤缴,俯钓长流”,将浑天仪的精密与田园诗的空灵熔铸成超越时代的智慧;袁宏道作《去吴七牍》,以“官场如戏场”的犀利,撕开晚明士人“市隐”风尚的序幕;郑板桥辞官潍县时挥毫泼墨:“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让一丛瘦竹承载起知识分子的清傲风骨。
在当代语境下重读这些历史片段,会发现惊人的现代性启示:陶渊明挣脱“心为形役”的觉醒,与当代人挣脱功利桎梏的追求遥相呼应;王阳明的“致良知”,与追寻本真的职场哲学不谋而合;范蠡的跨界转型,暗合多元发展的时代潮流。当我们讨论“躺平”与“内卷”时,先贤们早已用生命实践给出答案——真正的自由,在于拥有选择的勇气与智慧。
《越绝书》言“圣人行兵,上与天合德,下与地合明,中与人合心”,而历代文人的去留抉择,何尝不是“合德、合明、合心”的生命实践?辞职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确认;去留之间看似个人抉择,实则是文明基因的迭代传承。当现代人在职业困境中徘徊时,不妨听听苏轼穿越千年的吟唱:“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李威)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