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鲁迅先生化名唐俟,在《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6号上发表“五四”时期篇幅最长的杂文名篇——《我们怎样做父亲》。
文中提到,“……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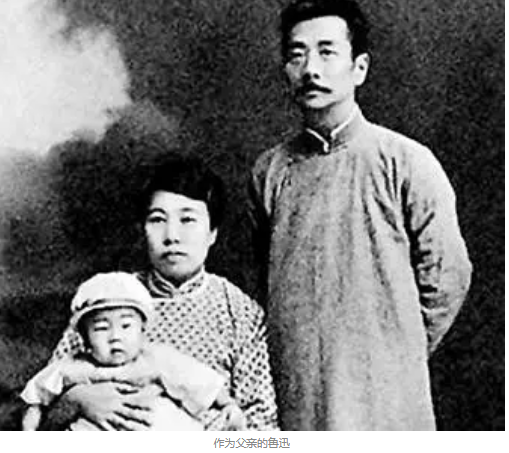
1910年,美国华盛顿州布鲁斯·多德夫人首先推广“父亲节”。114年过去,在2024年的父亲节,灵魂拷问声犹在耳:“我们怎样做父亲?”
回溯中国式父亲的养成史,就会明白这个话题的错综复杂,既关乎性别和亲子,更关乎传统和时代。
说父亲的话题,就不能只说父亲,而要说孩子、家庭和社会。
社会情境中,父亲既是家庭角色,也是社会角色。他首先是一个儿子,然后是一个丈夫,最后才是一个父亲。
在1910年代,也就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当时的中国家庭仍然是封建大家庭,父亲是绝对威权的家长,个人权利意识尚在萌动。
但与此同时,在新旧文化的缠斗中,个人的意识开始觉醒和复苏。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呼喊一个青春中国,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都是青年话语的时代声音。
在率先向旧文化发动攻击的同时,鲁迅那一代文化人还试图从文化角度重构父子关系,其实也是向传统宣战,希望父亲们能理解、指导、解放下一代,努力塑造“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从而让孩子,也就是年青一代创造一个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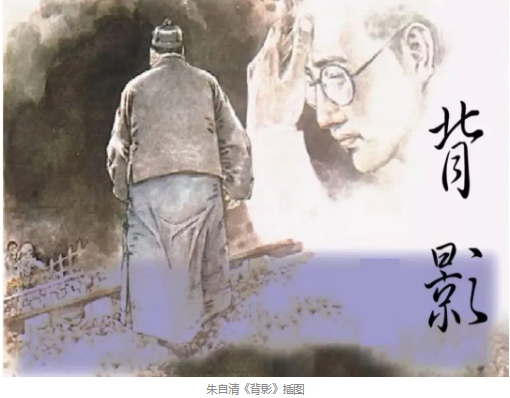
时光荏苒,1945年8月,为纪念抗战中牺牲的中国军人,上海申报刊文《八八父亲节缘起》,梅兰芳、颜惠庆等10人曾倡议以“爸爸”谐音的8月8日作为中国父亲节。1946年5月,潘公展、李石曾等知名人士再次联名向当时的国民政府请求设立中国父亲节。
又是70多年过去,在人们已经习惯于将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作为父亲节的当下,反观一百多年前的思考和呼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父亲其实还是那个父亲,时代不同了。
随着老龄化时代呼啸而来,在育儿负担日益加重的今天,在“传统文化热”不断升温的当下,父亲的角色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尴尬。所谓“丧偶式”“诈尸式”育儿,成为妈妈乃至社会贴在很多年轻父亲们身上的一道标签。
事实上,清末以降,伴随传统父权制的崩溃,父亲希望更多地参与孩子的养育,并倾向于采取宽容、温暖而不是严厉、专制的态度,形成了中国当代都市父亲角色的核心面容。
美国“爱家协会”创始人杜布森博士曾表示,父亲是孩子成长的榜样,而且重申传统观念里男人在家庭中应当承担 “供应者”“保护者”“领导者”“精神领袖”4个角色的职责。
所以,就整个社会体系而言,父亲必须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求得平衡。这与过去只需在家庭外部寻求成功的情境完全不同,这也给当代父亲带来更大的压力和负担。
对于细水长流的母爱而言,父爱往往是克制而冷静。这和传统文化有关,也和性别特征有关。就现实而言,这种差别其实不断在消弭,中国家庭的“严父慈母”氛围已有很大改变。

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亲?
首先,必须认清自身的定位和角色。你可以不是职场或事业的成功者,但必须是一个努力奋斗的前行者。奋斗,不一定成功,但不奋斗,永远不会成功。只有给孩子一个努力奋斗的印象,他们才会以父亲为榜样。
其次,要懂得沟通。要善于和孩子沟通,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做一个“不缺席”的父亲,让爱、宽容和学习成为家庭的主基调。
在生活中,既要昂首挺胸向前,又要学会蹲下来交流。只有与生活和解、与时代并进,才能融入人生的山海,走向广阔的未来。
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
我的父亲已经离去17年,墓木早拱。他是一个只读过小学二年级的乡村篾匠,但他热爱生活、重视家庭、关爱子女。
在起早摸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里,他凌晨早起送我上学的情景时时浮现,他辗转四五道农班车给我送米送菜的经历永不能忘,他敬老爱幼的品德始终影响着我。他不曾留下多少财富和资源,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天下最伟大的父亲之一。
最后,作为一个父亲,还应该做一个思想独立、人格健全的人。热爱生活、拥抱时代,用善意和良知引领人生、影响他人。
在这个父亲节,和天下父亲共勉!(安徽时评)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