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口铄金,三人成虎,如果一个人的劣迹被写入中学课本,大概更没什么翻身的机会了吧?陈西滢差不多算是这么一个人。
中学课本里有鲁迅的大作《藤野先生》,里面有一句:“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文末注释里写得很清楚:“正人君子”之流指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御用文人陈西滢之流.。
这个注释是要考的,所以我记得牢,一想起陈西滢,马上心里就跟着出来一个后缀“之流”。后来去复旦读作家班,忘了是听陈思和还是陈引驰讲周作人,又提起陈西滢跟周作人的一段公案,1925年,在陈西滢、鲁迅、周作人围绕着“女师大”而起的大混战中,周作人揭发陈西滢曾经说过“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叫局”。
所谓“局”,酒局也,所谓叫局,朝好里想,就是前段时间里一度引起哗然那篇《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还能叫吃饭吗》里所言,叫个姑娘,如同多加一道菜,朝不好里想,则是暗喻女学生兼做性工作者。
堂堂教授,说话如此轻佻,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本来对陈西滢就没好感,看到这句,更是雪上加霜。周作人虽然是个汉奸,却一向是帮女人孩子说话的,他揭露陈西滢的真面目,当然是一种正义的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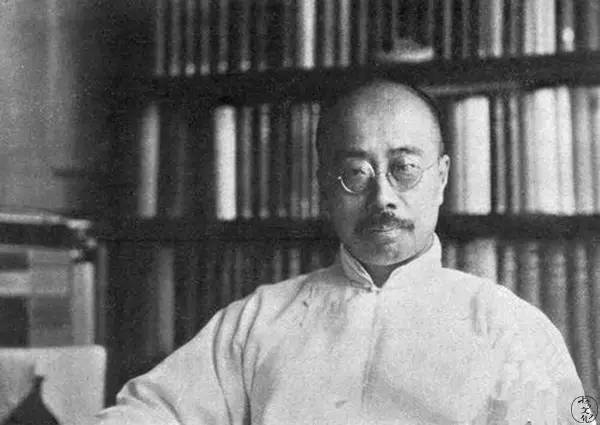
许多年之后,有些想法不觉间改变,回头重看这桩公案,似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周作人对于陈西滢的“揭发”,并非孤立事件,要放到时代的背景下去看的。
陈西滢和周作人以及鲁迅这兄弟俩起冲突,与“北师大风潮”有关。关于这件事,我们中学课本里也略略透露了一点,《纪念刘和珍君》里写道:“她(刘和珍君)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
又说“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这段话明写刘和珍的仪表风范,同时也暗写杨荫榆“广有羽翼”,这羽翼还很凶残,将那么温和的刘和珍强拖出校。曾几何时,鲁迅在学生心中代表着绝对正义,那么,杨荫榆和刘和珍之间的黑与白、是与非也就一清二楚了。
但事实上,这笔账并没有那么清楚,杨荫榆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上任于1924年2月,当时还叫“女高师“,同年改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
这身份听上去很体面,但这活并不好干,杨荫榆当上校长之后,便和学生们冲突不断。许广平说:"她整天地披起中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以外,回到学校,不是干涉一下子今天用几多煤,明天撤换什么教员,一屁股往卧室一躺,自然有一大群丫头、寡妇,名为什么校中职员的,实则女仆之不如,然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有时连食带闹,终宵达旦,一到和各主任教员周旋,和学生接谈,都是言语支离,问东答西,不得要领的糊涂虫,学生迫得没法,由各班推举代表去见她,要求她自行辞职……"
听上去确实不怎么样,但所谓“言不及义、言语支离、不要领的糊涂虫”都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感觉,如果这种说法可以叫人辞职,那么很多认只怕都职位难保了。
学生还指控她假公济私,庇护跟自己有关系的学生,但这个罪名能否落实、以及怎样处罚,也需要一个过程。可双方却已经都等不得,轮番互相攻击,此起彼伏的风波,引起文化人的注意,陈西滢率先开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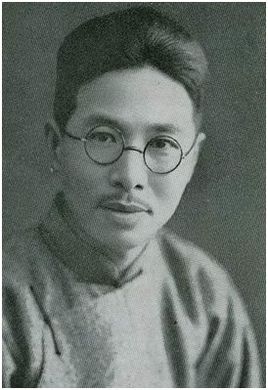
他说:“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的风潮,也酝酿好久了。风潮的内幕我们不很明瞭,暂且不欲有所置议。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于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
这段话看似公允,但以学生为是校长为非的氛围中,似乎有点不合时宜,鲁迅就怀疑陈西滢是杨荫榆的亲戚,后来陈西滢还专门给徐志摩写信分辩过。鲁迅确实多想了,如果我们一定要做诛心之论,倒不如猜测陈西滢是因为杨荫榆的被驱逐而生出兔死狐悲之情。
邵建的著作《瞧,这个人》里提到,从1919年到1922年,学生驱逐拒绝校长事件频发,在当时,“学生开除校长,在学生看来是自己当仁不让的权力”,似乎校长已经变成弱势群体。
陈西滢虽非校长,但是应该也能感到来自学生的压力,加上他曾经留学欧洲,更为注重程序正义,站到杨荫榆一边在所难免。
但他这一表态,意味着他和鲁迅他们就此友尽。1925年5月底,鲁迅等七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支持学生,陈西滢再次表达不以为然,说:"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茅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陈西滢这话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从头到尾,强调的都是事实二字,用现在的话就是,他认为眼下情绪太多,事实不够用了。但接下来他却又开起地图炮,指责“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偏袒学生,明摆着剑指鲁迅、周作人等人,这就有点对人不对事了。
周作人立即应战,正是一团混乱时候,一向脑洞极大的徐志摩忽然写了篇文章,不无饶舌之嫌地夸奖陈西滢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士派的'兄弟'们"。
这其实是一句闲笔,却被周作人抓住了,于是,周作人说,陈西滢跟人说过,现在女学生都可以叫局。
那时候女权主义虽然还没像现在这样轰轰烈烈,这一句话也足以把陈西滢打进十八层地狱,陈西滢大声叫屈,说他不过是闲谈中感慨女学生居然也可以叫局,并没有说“都”,周作人则说,他那里有证人,虽然这个证人因为胆小怕事,不愿意出头。
他说的证人是张凤举,张凤举原名张定璜,和周氏兄弟一向过从甚密,据说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跟鲁迅翻脸时,张凤举就在现场劝架。这是后话,反正许多是非中都有他的身影,鲁迅去世之后,苏雪琴给胡适写信大骂鲁迅,胡适为鲁迅辩护时,也提起,陈西滢会指控鲁迅“抄袭”,是误信了“小人张凤举”的话。不知道这说法是否冤枉了张氏,但很奇怪,有些人就是每每落入这种尴尬境地。
但是也有愿意出头的,有位川岛先生说他也听说过,并表示愿意站出来作证,周作人却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了。按照周作人的说法,他所以叫停,是出于对陈西滢的极度不屑:“不耻敌多,但须选为敌之人,如有卑鄙之敌,即此已是败北,已是耻辱了。”
这跟他哥哥喜欢痛打落水狗似乎不太一样。但我总怀疑,理由并不止于此,周作人不想继续纠缠“叫局”一事,与其说他清高,不如说他明白,当他发热的大脑渐渐冷静下来,就会知道即使陈西滢私下里说了这句话,也不应该成为被指控的理由。
谁不曾于私下里,于两三知己、亲朋好友面前说过偏激的的话?在谁面前说的,就只对谁负责,听者可以鄙夷他,可以跟他友尽,却没有权力把这个话拿到大庭广众之下作为呈堂证供,否则,即便亲朋好友之间谈话,也要时刻“斗私批私一念间”,要把每一句话说得无可挑剔,那多可怕,一点容错率没有的世界有多可怕。
更何况,陈西滢矢口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起码可以视为,他的公开表态是,他对“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一说法是不认可的,这就足够了。如若周作人继续抓住这句话做文章,他犯的错误、制造的恐怖,就比哪怕是说了这句话的陈西滢严重多了,周作人后来不肯再提,也是明白了这一点吧。
这段公案已成既往,却不可以当成陈芝麻烂谷子视之,也不可简单地定义为或黑或白,其间有太多值得咂摸的东西,所谓鉴古知金,中间并不需要隔着太长的时间。
(未经大皖和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欢迎微信朋友圈转发。)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