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有个女孩子看我经常写阜阳,特地从合肥跑过去。下了车,她问当地人哪里有好吃的,当地人说,“liufang有个小吃街”。她就想着,“liufang”具体是哪两个字呢,是“六坊”吗?后来她又通过微博私信这样问我。
我哑然失笑,哪有这么古雅,就是“阜阳市第六纺织厂”的简称而已,这地方我曾经再熟悉不过,后来就隔着一段距离,闻听它的衰落以及以各种方式再度繁华,比如说,变成这著名的小吃街。
我妈是六纺的老工人。她十八岁那年,六纺到他们村去招工,和我姥姥颇有些芥蒂的我姥爷的族人,叮嘱村干部,不要把表格给我妈。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村干部偷偷塞了一张表格给我妈。
多年后村干部进城打工,我爸帮他谋了个看大门的差事,现在他成了正式工,有了养老保险,勿以小善而不为这句话实在对,你不知道恻隐之心一动,会埋下怎样的伏笔。
但是我妈刚来到六纺时是傻眼的,她在农村虽然缺吃少穿,却落个自由自在。到这里一天八个小时,不能有片刻掉以轻心,像坐牢似的不说,那工作也着实辛苦,在纺织机前跑来跑去,我小时候就常听我爸感叹:“你妈一天最少要跑六十华里,也就是三十公里”。
环境也很差,机器声隆隆,当面说话都得扯着嗓子,毛絮乱飞,到了夏天,没有降温设施的车间里,更是酷热难当,我妈由不得在心里对自己说,完了,掉坑里了。
可也不带再回去的,回去让人看笑话吗?只能咬着牙朝下做,直到近二十年后,她得了肺病,才从纺织车间调到检验车间。
 纺织女工老照片(网络图)
纺织女工老照片(网络图)
即便如此,那时的六纺还是让多数人羡慕的所在,收入好,福利也不错。我妈进厂后就分到一室一厅,之后她结婚,生下我和我弟,加上我爸我奶奶,我们一家五口人,栖身于那三十平米的空间里。
我五岁之前都住在那里,整天跟着一群孩子在偌大的宿舍区跑来跑去,不知道是我动作慢还是人缘差,动辄他们就跑得无影无踪,我一个人呆呆地站着,感觉到被排斥的失落和委屈。
有时候,我终于跟上他们,从我家住的宿舍区边缘跑到深处。那里有好几排筒子楼,我们从黑暗的这一头钻进去,路过放在走廊上的各种煤球炉子和锅灶,躲过影影绰绰的身影,再从光明的那一头钻出来,感觉非常魔幻,像是穿过一个魔法城堡。
我多么羡慕那些住筒子楼的小孩,尽管我爸妈一再说,我们家的房子更好,我还是觉得筒子楼更魔幻,住在里面的人,声息更相通,用现在的话说,更有一种集体主义的朴素浪漫。
六纺的各种设施也很全,比如澡堂。我家搬走之后有很多年,我还是经常到六纺澡堂去洗澡,感觉比外面的澡堂客源单纯,因此更干净,再说厂里还经常发澡票。
检票口卖点小杂货,梳子搓澡巾香皂袋装洗发水之类,也卖橘子汽水,洗澡出来,来一瓶橘子汽水,是无上美味,瞬间弥补了被蒸发的水分。如果是冬天,那一丝凉凉的清甜,可以抵达从上到下所有神经末梢。
还有电影院,我在六纺的电影院看过《笔中情》,讲书法家赵旭之的爱情,刚才百度了一下,这电影居然是在《西游记》里演唐僧的迟重瑞和演小白龙的王伯昭主演的。
看过唐国强主演的《孔雀公主》,潘虹主演的《杜十娘》。我奶奶大爱《杜十娘》里的台词,有时候在阳光下做着针线活,也会悠悠地念出一句。
 《杜十娘》剧照
《杜十娘》剧照
我奶奶这做派有点抓马,在我之前,她已经有了十来个孙辈,但她似乎依然没习惯做个祖母,不会像我姥姥那样,会时不时塞给我一点零花钱,把好吃的都省给我。
我奶奶是自我的,她一辈子心里都住着一个少女。我整个童年都与她不睦,但她也不能说对我全无馈赠,她对于带有戏剧色彩的一切的爱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还记得,她挂在嘴边的那些民间传说、戏曲段落,丰富了我幼时的精神世界。
最初的童年阴影,也是在六纺留下的,厂里有个女工被高压线打死了,似乎是工伤,在厂里举行了规模极大的葬礼。我奶奶带着我前去围观,有一个女人放声嚎啕,我奶奶说这是逝者的姐姐。一直到现在,我从高压线旁边走过,还是胆寒,即便知道,并没有那么不安全。
我五岁之后,我爸单位终于分到房子,全家从六纺搬离,但那间小房子还属于我妈,我妈上夜班之前,或是下了中班之后,会去那里休息。后来我姥姥进城,也住在那里,所以我还是常去六纺,随着我逐渐长大,理解力增强,在这里,我对生活有了更多认知。
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六纺人被派到伊拉克工作,这是美差,当时厂里工人月薪五六十块,到了伊拉克,一两年间,就能荣升为“万元户”。但是,不是有句俗语吗,男人一有钱就变坏,我妈一个姐们的丈夫从伊拉克回来就提出离婚,姐们一番侦查,发现他有了小三。
那段时间,那间小屋里,每晚会坐满我妈的女同事,她们义愤填膺,休戚与共,众口一词地痛骂陈世美,我那时才发现,这些看上去平凡的阿姨,原来有着如此丰富的词汇,精妙的表达,在花样翻新的咒骂中,她们的面容熠熠放光,从不曾如此美丽。
其中有个晚上,她们又一次地在小屋里讨论得水深火热,忽然,有人注意到窗外出现一张黑沉沉的脸,是那个“陈世美”。“秦香莲”走了出去,他们一起消失在夜色中。屋里的人都有些沉默,然后,互相询问:“我刚才没说什么吧?”“我也没说什么。”
魔法消失了,现实感让激情荡然无存,夜一下就很深了,她们的脸上有了一丝丝破败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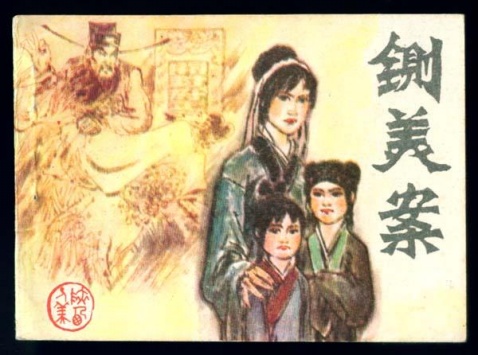 《铡美案》
《铡美案》
我总是周末去,周一早晨坐厂车上学,厂里有好几辆车将厂区的学童送到四面八方,漂亮的大巴车车身上印着三个字,有几年我念成“哈雨演”,后来才知道是“哈尔滨”。我姥姥总是将我送到车门前,有时还会红了眼圈,虽然分别不过一个星期,但我姥姥不是感情炽热嘛。
这种炽热是一种双刃剑,一旦她发现被背叛就绝不原谅,我读初中时,有次回六纺找当年的玩伴,没去我姥姥家,怎么就那么巧被我姥姥隔窗看见了,隔着一条街,她来不及追赶我,当天晚上,就跑到我们家,把我大骂一通。
好的,说说我去找的那位玩伴,她比我大几岁,是个文学爱好者,能背《红楼梦》里所有的诗词,我到现在也背不下去,也不打算背下来。
她还能背许多唐诗宋词,尤其爱好李商隐,同时她是一个体育健将,扔铅球掷标枪全校第一。她生得也美,身材纤长,她有个姨妈特别疼爱她,花很多钱打扮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她穿了一条粉色的真丝缎裙,像个模特一样飘飘欲仙地和我走在六纺的大街上,引得不少人回头。
那时,我觉得她从头到脚都充满了优越感,追她的男生也很多,然而她中学毕业之后,还是和大多数六纺子弟一样去了纺校,毕业后可以进厂,得到一个铁饭碗。
也有人对我妈说过:“你真傻,怎么不让你闺女上纺校。”我妈说,她从未想过让我上纺校,她累了这一辈子,还不够吗?再说,在我们家,育儿这件事归我爸负责,她不想操太多心。
女伴也当了两年工人,那两年她迅速发胖,她苦着脸说:“没办法,我不吃跑不动。”我就此对过劳肥这个事有了了解。后来厂里的业务每况愈下,女伴下岗,跟她的丈夫去街头卖小吃,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震惊之极,无法想象当年那个诗情画意的女孩,会这样步步走低。
好在,又过了一些年,我听说,女伴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开了几家分店,很多人从外地驱车而来,就为了去她的店喝一碗“咸马糊”——吾乡的一种特色小吃,她现在,在阜阳的餐饮业已经很有些名气了。
你看,喜欢《红楼梦》爱背《古诗词》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吧。
 《红楼梦》书封
《红楼梦》书封
我成年之后很少再去六纺,我妈那间小房后来被拆迁了,补偿了一套两室的新房,给了我弟弟,有天我弟弟一高兴,把那个房子给卖了,我和六纺的缘分也断了。有时经过通向六纺的路口,会朝那边望一眼,成排的楼房,像海市蜃楼一样浮现在那里,但都与我无关而了。
二十三岁,在我彻底离开小城之前,有熟人请我吃饭,约在六纺,说是原来靠近厂区的一排门面,现在做成了酒吧街。
我赴约而去,看见一个个装修得挺洋气的门脸,风情得有点套路感的老板娘。我坐在其中一个包厢里,想起当年,墙的那一边有许多个车间,终日机器声轰隆。我曾经进去过一次,像别的女孩子那样给妈妈送饭,那天电闪雷鸣,一个炸雷打下来,我手里的饭盒哐当落下,我也滑倒在地,不由大哭起来,我妈的同事路过,将我扶起,混乱中,我遗失了脚上的凉鞋袢儿。
她带着一瘸一拐的我走进车间,跟人介绍:“这是大个子的女儿”,我妈大概一米六七,在厂里已经有“大个子”的名声,可见中国人这些年真的长高了。没有来得及赶回家吃饭的我妈看到我很高兴,看我这么惨又很心疼,用个瓷缸子打来冷饮,不过是冰镇糖水,工人劳保饮品,但是在没有冰箱的当年是个稀罕物,我觉得那一刻的我妈比平时慈祥,也自此觉得车间是个美妙的地方。
吃完那顿饭我就去了省城,其间十多年,不再听到酒吧街的消息,倒是有一次我问家人哪里有小吃,他们都说六纺。
于是某个早晨,我特意驱车来到六纺,物也非人也非,筒子楼不再,热闹的车间已不再,我妈妈那些工友的欢声笑语已不再,含着泪把我送上大巴车的姥姥也不再,那些玩伴,也像散落的花儿,流落四方。
然而,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还有有一种熟悉的气息围绕着我,让我恍惚,几乎要掉下泪来。我像个没头苍蝇似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看见墙,看见墙上的宣传语,好像吃了一些小吃,但是你要问我吃的是什么,我真的,一点也记不清了。
 作者 闫红 (未经大皖和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 闫红 (未经大皖和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