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第一次装修房子时,考虑买个洗碗机,我跟我妈一说,她毫无前兆地勃然大怒了。具体怎么说的我忘了,近乎东北老母亲的那句灵魂发问:“你看我一个洗碗机?”
没想到就这么触碰到我妈的道德底线,在她眼中,似乎买洗碗机,不只是一个消费行为,还是个道德行为,悍然提出买洗碗机的人,很可耻。
跟我妈商量不通,我自己跑到电器商场去,遍寻不着,试着问了几家,售货员无不感到匪夷所思:“洗碗还要用机器?三两下不就刷好了?”我在她们的脸上认出我妈的表情,当然,她们要温和一点。
为了不自绝于人民,我放弃了装洗碗机的年头。
十多年之后,我装修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对于洗碗这件事的厌恶,已经让我甘愿背负道德压力。但我到底是个胆小之人,不敢理直气壮地在这上面花太多钱,缩手缩脚地在网上买了个两千多块的台式洗碗机,垛在北阳台上的水槽边。
 (网络图)
(网络图)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使用洗碗机的情形,家人脸上都有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本来就不爱看说明书的我,更加地手忙脚乱,一通操作猛如虎,好在洗碗机的操作模式简单,两个按键搞定。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但听里面又是洗又是漂又是烘干,忙忙叨叨的足有两三个小时。
我能忍,我妈不能忍,她比洗碗机还忙,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一会儿起身一会儿坐下,好像眼前有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她已经做了足够的明示和暗示,人家就是不起身告别。
洗碗机不看她脸色,我得看,我妈每个动作,都让我的良心备受煎熬。
等到洗碗机终于长叹一口气安静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高脚杯倒是洗得挺干净,盘子里却是一汪水,和面的大碗上面糊犹在……我被当场打了脸。道德与智商双破产,家里人脸上都是耐人寻味的微笑,让我心虚气短,然后恼羞成怒。
洗碗机就此被搁置。人家再说洗碗机,我就会给予过来人的劝告:“千万别买洗碗机,不适合中国国情。”说来这个洗碗机帮我省了不少钱,我再想买破壁机榨汁机这些新科技时,它就会跃出脑海,扑灭我熊熊燃烧的购物欲火。
又过了两三年,跨年夜,朋友圈里照例有很多年度总结,有个朋友历数她这一年做的增加幸福感的事,其中一件就是买了个洗碗机,选择快洗模式,四十分钟搞定,洗得超级干净。
我被提醒了。找出三年前收在抽屉里的说明书一看,我这个洗碗机快洗模式只要三十分钟。说明书上还展示了碗碟的摆法,我三年后才想到,碗口朝上当然会积水。说明书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可惜这世上大部分东西没有说明书,比如婚姻和育儿。
总之,暌隔数年之后,仔细阅读过说明书的我重新启用洗碗机,像是启用一个谪臣,然后发现,人家真是太能干了。
 (网络图)
(网络图)
这个洗碗机看上去不大,但是很能盛,大锅确实放不下,不过,相对于洗锅,洗碗难多了。我妈她们洗碗都是先洗后漂,第一遍下来,那个水浑厚无比,难以直视。我习惯一次把一只碗彻底洗净,非常浪费水,然后还要放置晾干,不然就成为细菌培养钵,特别麻烦。锅是在高温状态下使用,自行消毒了,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锅是可以手洗的我觉得。
油腻腻的碗碟放进去,亮晶晶热乎乎完全干燥的碗碟拿出来,真的感觉极度舒适。要什么田螺姑娘,我更爱洗碗机这种没有感情不需要互动的机器。
从此成为洗碗机的重度依赖者,一个房子,装修得再好,若是没有洗碗机,在我看来都是重大缺陷。这次疫情期间,一台洗碗机更是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幸福感,我在朋友圈里,不下三次看到朋友为洗碗的事跟伴侣吵架,是啊,洗碗事小,却关系到家庭整洁与安定的大局。
通常,洗碗是所有家务的第一步,不洗碗,就没法抹桌子和拖地。但洗碗是最烦的,你就坐下来拿起手机刷着微信做心理建设,越做内心越崩溃,最后,你的内心和环境一样乱糟糟。
若是有一台洗碗机,就会形成一个良好开局。上种红莲下种藕地把碗碟摆放进去,桌面有了眉目,清理起来很easy,擦桌子、拖地势如破竹,攻城略地不在话下。
亲手洗碗虽然看上去更加勤劳朴实,但是你可能并没有这么高风亮节。我们最好是按照自己最疲惫最懒惰时的状态去安排生活,而不是正相反。我有个朋友装修时秉承“用时间换空间”之道,买了个可以收起来的床,没过一个星期她就失去了把床收起放下的耐心,那个床地老天荒地摆在那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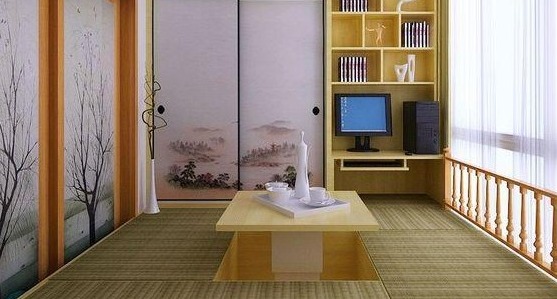 (网络图)
(网络图)
我还曾在客厅打过一个榻榻米,想象中的我盘腿坐在上面喝茶,跟朋友坐而论道,事实上由于没有台阶,我上去一次都觉得麻烦,那个榻榻米在我家最好的位置庸庸碌碌地积满了灰。
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完人,这是跟这世界的相处之道,也是跟家的相处之道。
总之,用不用洗碗机,其实跟道德一点关系也没有。它最多牵扯到一个价值判断:“我花时间和精力做这件事到底值不值”。有个朋友说,很多家庭矛盾的核心就是总喜欢把价值判断上升为道德判断。你只是认为这件事没价值,对方却觉得你这样想就不道德,那就没法聊了。
 作者 闫红 (未经大皖和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 闫红 (未经大皖和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