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振强散文集《村庄令》里的作品是清新的、纯净的,亦是一脉贯通、文韵悠长的。同样是写一方天空、一片田园、一座村庄、一群亲邻,魏振强能将深重的、浓稠的、缱绻的情感以朴拙的、坦诚的、轻浅的方式氤氲于字里行间,率真中见诗意,醇厚中溢善良,悲苦中寓坚韧,念想中盈感恩,伤怀中透希冀……生动再现了一个时代的人情之美与人性之美。
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曾言:“你的童年是个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那个叫“大司村”的地方,明明“小”得可怜,然而,作者却被迫从5岁那年懵懂踏入,跟着孤寡的外婆艰难过活,从天真柔弱、不谙世事,到胆气渐壮、青春勃发,其间虽是栉风沐雨,经霜历雪,却又从外婆与乡邻身上,从田畴与山野之间,感受到太多的善意与美好,收获了无尽的温暖与希望——哪怕在回首时恍如一瞬,他却真真切切地知道,那里潜藏着再也回不去了的13年时光!大司村亦真的很“大”,因为恰如诗人说得那般,即便数十年过去,作者仍旧“走不出它的边际”——这本《村庄令》便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说,写杂文的魏振强属于“辛辣派”,那么写散文时,他似可归于“冲淡派”。作家刘震云尝言:“凡是用特别复杂的文字(形容词和副词等)在写作的人,都是没文化的人。如果外在特别复杂,里面的内容一定特别干瘪。”纵观《村庄令》中的各辑佳作,无论是首辑《夕阳下山岗》、次辑《第一场霜》,还是第三辑《模糊的面孔》、末辑《外婆,安好》,均是真诚的,朴素的,也是简约的,克制的,一点儿也不“复杂”。很多篇章,作者采用近乎白描的手法,以大笔点染之,粗线条勾勒之,少粉饰而真意自出,不雕琢而真情灌注。权以首篇《夕阳下山岗》为例——
夕阳的余晖与山岗的轮廓,真切而恍惚,美丽又压抑,奠定了整篇文章的情感基调,而这一景象的反复呈现,不仅是时间与地理上的坐标,更是情感与记忆的载体。诚然,每一次眺望,都是对亲人的期盼。一个5岁孩子对父母的切切思念,在那循环播放似的夕阳余晖中被无限延展开去,静默的山岗宛如一座连接血脉亲情的坚固桥梁,承载着遥不可及却又从未断绝的希望……
而作者通过对前往小姨娘家途中诸多景物的描绘,如坟地、山洼、水库等,既巧妙渲染出孩子难以言表的恐惧,又深刻映射出他对陌生环境的好奇,以及深埋心底、转身回家的复杂情感。结尾处,当父亲终于在夕阳下山岗的背景中步步走近,漫长的等待也终于有了回应时,那简单的两句对白,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情感的爆发已达到了顶点……
不难发现,外婆从一出场开始,便自带“主角”光环,她既是作者童年的至亲、成长的守护者,又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更是那个时代无数乡村女性的典型缩影——勤苦、善良、隐忍、自尊。随摘一个片断:“一天中午,我在家里等外婆吃饭,等到别人快上工,也没见她回来。我就跑到那块地里。太阳太毒了,我光脚踩在土里,脚下像火一样的烫。外婆瘦小的身躯弯曲着,她正在给山芋垄松土,胸前和背后印着大块大块白色的汗渍,我朝她打招呼,她的嘴巴已经干得说不出话来,嗓子肯定像沙地一样烫。”此处无声胜有声。
外婆对“我”的爱与关怀,对“我”的教育与引领,是简朴的、“土气”的、“笨拙”的,亦是深沉的、无私的、伟大的。无论是“我”跟她下地干活,还是独自求学他乡,亦无论是日常的接人待物,还是意外的遇困受挫……外婆在,爱就在;外婆在,榜样在——正如作者在《外婆,安好》中动情坦言的“我甚至想过,如果她身上的骨头能给我们做柴火取暖或者做一顿饭,她一定会二话不说,任我们拿去点着。”
往事酿酒香,故人入梦甜。除了最亲爱的外婆,作者同样以简洁又细腻的笔墨,为我们铺绘出一系列“面孔模糊”却记忆犹新的乡村人物群像。“我一再告诉自己:不虚构、不夸张,不矫情,这样才可能保持对一座朴素、朴实村庄的起码尊重。”(见《后记》)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或为亲友,或为旁邻,或为玩伴,在作者笔下皆是立体的、丰满的、独特的。尤其是,他们真诚、仁厚又良善,他们执着、顽强亦乐观……那些源自乡野、与生俱来的美好品质宛似山林间的涓涓溪流,早已融汇进作者的血脉,化为不可或缺的成长力量,亦若村庄上空的点点星辰,熠熠闪耀在生命的晦暗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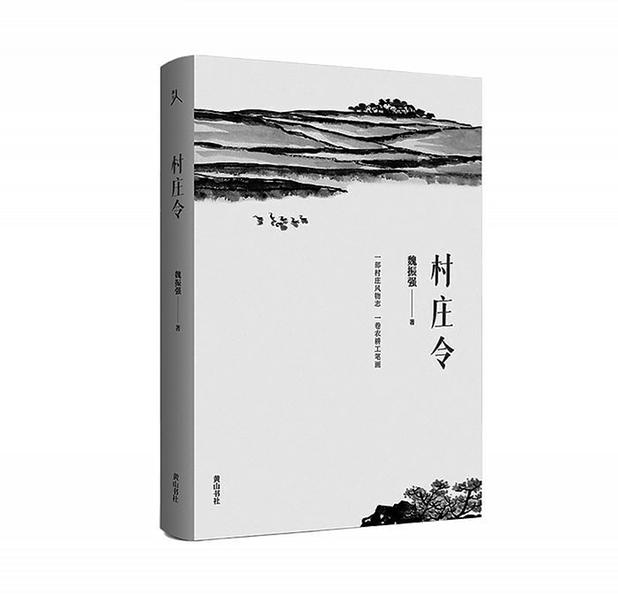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