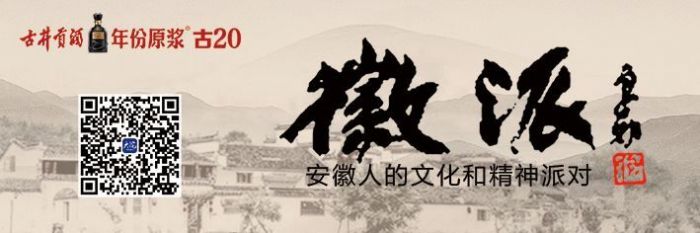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 上周五,省作协主席许春樵做客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的大皖客户端“徽派”,围绕正被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疫情,许春樵从“以人为本”、“悲剧审美”、文化差异等方面进行了个人化的梳理。
A “以人为本”该是归位的时候了
 许春樵
许春樵
徽派:应该也是很久没出门了,通过直播镜头跟很多想见而不得见的老朋友打个招呼吧!
许春樵:各位徽派的朋友,大家好!疫情还在,除了非常必要,现在更多是在网上办公,今天我们就在网上隔空聊聊天吧!其实真正的朋友也不一定要天天见面喝酒,有些东西在心里记着、念着,未必非得通过某种形式来嫁接。
徽派: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疫情信息的?
许春樵:当时我在澳大利亚,14号过去的,19号听说国内买不到口罩了,20号钟南山公开“人传人”的事实,22号到上海浦东机场入关就开始检测了,23号武汉封城。回来后有些懵,一下转不过来弯,在那边看澳网,到处是沙滩、阳光以及自由行走的人们。刚回来还在筹划过年串门喝酒的事情,可成批量的饭店除夕年夜饭被取消,医护人员年三十奔赴武汉,紧张的情绪在年头岁尾四处弥漫,年初跟武汉的一些朋友打电话,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那里有很多文学界的同行,还有我的一些同学,给我华中师大的导师打电话,老师也说情况非常不好。其余没说,是因为说不下去。这是场天灾。
徽派:这场疫情中,您的生活和思考有哪些方面的改变?
许春樵:这场天灾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一些生活观念。
改革开放40年,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在家里待两个月,平均数应该是两个月左右;从来没有这样认真休整和休息过两个月。我们一以贯之的日常生活方式被颠覆了,居家出不了门,商店开不了业,工厂开不了工,单位开不了会,学校开不了学,节后上不了班,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让人猝不及防和手足无措。冷静下来思考,这些生活方式改变的同时是我们生活观念的改变。
徽派:比如说?
许春樵:比如说,在家待着,钱没用了。有钱买不到东西,有钱救不了命,在武汉,患者家属愿意倾家荡产,用家中所有的钱,来救父亲,救儿子,救妻子,救丈夫,可医生说,没有特效药,与钱无关。医生尽力,患者认命。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天灾面前,金钱、权力、荣誉、地位都是微不足道的,疫情铺天盖地袭来时的束手无策,这更彰显了人类自身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这个时候,我们才想起了“以人为本”这四个字,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首先是健康地活着,可这几十年来,大家虽然都认同以人为本的理念,但并没有落实到灵魂深处,没有扎根于具体生活中,以人为本更多的是以概念的方式出现在体面的讲话和华丽的文章中。白加黑、五加二、孕妇到一线,生病不下火线等极端例子常常被推崇,当我们用玩命的方式去创产值、赚钞票、干事业的时候,就不是以人为本了。
徽派:“以人为本”没有落实到每个生命个体。
许春樵:是的。面对拼出来的成就,疫情时期让我们思考的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但如果健康没有了,生命都没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么多年,我们实际上追求的是以钱为本,以物为本,以利为本,在历史转型期,这是必然的,但代价太大,好多乡镇干部、基层一线的创业者们,为了干成事拼命加班,拼命喝酒,有的喝死了,有的累死了,还有相当多的人都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的状态。我们牺牲了一代人甚至是两代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在这次疫情面前,我们会悟出:活着才是人的根本。活着是最低的底线,也是最高的价值。这次疫情,切身感受到,以人为本该是归位的时候了。
B 抗疫成果是东方文化的胜利
 徽派复工首期走进作家许春樵家中
徽派复工首期走进作家许春樵家中
徽派:疫情中,外在碎片化的信息和宅在家中的恐慌,让很多人都处在焦虑当中。您这段时间有焦虑过么?
许春樵:我的焦虑是轻度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写作,这段时间静下心来写长篇,焦虑被写作稀释了不少,但对于整个形势的担忧还是有的。你说的焦虑,是集体性的焦虑,每个人在这次疫情面前不可避免地焦虑和恐惧。外围其它省份的零数据越来越多,焦虑就减轻了,这个转折应该是在三月初。现在新的焦虑又来了,输入性的病例可能会带来疫情二次爆发,因为欧美已经失控,这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
徽派:您怎么看中西方对于疫情控制迥异的态度?
许春樵:为什么中国控制住了,日本控制住了,韩国也控制住了,这些东方的国家都控制住了,欧洲、美国却失控了?进一步地深入思考,我发现了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疫情在东西方的两种走势与结果。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因为这都属于东方文化圈,儒家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基因,其主要特质是,他人意识、团体意识、大局意识和天下意识,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我们传统的文化伦理中还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家里遭遇灾难和不幸,长兄就是父亲,长嫂就是母亲,这是都是属于不想着自己,而想着大局、他人和天下。先解放全人类还是解放自己?西方是先解放自己,我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才有,我没发病,凭什么戴口罩,戴口罩是侵犯人权;而中国儒家文化中讲究的是“以天下为己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天下不安宁,我何以安生,先解放全人类后解放自己的理念在中国能推销出去,显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意识一脉相承。日本也是,政府一个号令下来,所有的人主动关门,主动回家,主动隔离,如果我们不能拯救他人,最起码不要影响他人,不去祸害他人,这就是他人意识、大局意识。美国人意大利人不行,只要我没发烧,没倒下,就得要去喝酒喝咖啡,要去跳舞,还反对戴口罩,好了,这下失控了。意大利比安徽省还小,却已经病逝了上万人。我的思考是,这次东方疫情的控制与成效,是东方文化的胜利,西方的失控,是个人主义、自我中心、自由至上的文化失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是没有绝对自由的,当人生活在一个群体中时,你就必须要交出去一部分自由,比如疫情来了,在公共场合你必须要交出不戴口罩的呼吸自由,还有跳舞的自由、喝酒的自由。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以人权反抗神权,几百年下来,个人感受和体验的神圣性是不容许侵犯的,强制戴口罩就上街游行抗议,中国封城封路、测体温、严禁出门,所有人自觉配合,没有人说侵犯人权了,东方文化中的隐忍克己,可以做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极致。
徽派:确实。这个与国民素质并没有必然联系。
许春樵:与素质无关,与文化有关。有人说,日本国民素质高,那么意大利、法国、德国人的素质不高吗?显然不是,那么多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出产的。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优势,我无意于否定西方文化,只是想说每一种文化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时期会显示出特殊的力量,没有哪一种文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权威和真理。以儒家文化为传统的东方文化在这次疫情中展示了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C “命运共同体”概念下的人类

徽派:我们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在疫情时期怎么理解?
许春樵:在灾难面前,我们应该使用人类的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诸如中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现在国际上有不少不和谐的声音,说这次疫情是“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不厚道、不善,甚至是恶毒。病毒无论从哪儿起源,地域和地域里的民众都是受害者,都是值得同情、关心和帮助的,因为这是天灾,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主动释放传播的,要中国道歉、认罪、赔偿,愚蠢荒谬,丧尽天良。现在特朗普好像脑子清醒了一点,不用“中国病毒”了,但是国务卿蓬佩奥还在说。中美之间有很多利益冲突,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很显然有借题发挥、故意报复的嫌疑。把受害者说成是施害者,其实就是吃人血馒头。
徽派:意大利法国很多激进人士观念也转变了。
许春樵:人类在疫情面前是同命运共呼吸的,是绑在一起的。以前有个说法叫地球村,我们在宇宙里就是个小村落,在瘟疫全面流行时,就是漂在大海上的一船难民。这个意识应该强化,自相残杀、挞伐是没有意义的,灾难面前,贸易战你还能打?店关门了,工厂停工了,订单取消了,贸易都终止了,你还打什么贸易战?我们要重新认识人类的命运问题。
D 灾难中我看到了“崇高感”的还原
 许春樵做客徽派聊疫情期间的感受和思考
许春樵做客徽派聊疫情期间的感受和思考
徽派:您说的这些确实扩大了 我们对于疫情的认知。那么回到您的作家身份。这个过程期间,你每天也在看新闻,作家的敏感度和敏锐度,会被哪些信息勾起。
许春樵:很多事情触动我感染我,甚至成为写作的资源。疫情期间我看到了灾难面前人性的向善,以及崇高感的还原与实现。当人们在无助和无望中呐喊与呼号的时候,人性的善被激活、还原和唤醒,十四亿人,甚至是我们平常不待见的吝啬者、自私者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受难同胞的关切、声援、帮助。这些年我们看到的负面的东西太多,在以钱为本、以物为本和整个社会疯狂逐利的背景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唤醒的是人性的恶。中国传统文化有两派,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性恶。人的个人道德,在一个命运与共、险象环生的环境下,善会被唤醒,人的恻隐之心,悲悯之心会充分表达出来,于是我们看到了湖北有那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那么多的医护人员,明明知道很危险,还是直接扑了上去,武汉中心医院牺牲了多少医护人员,那么多志愿者年都不过了,直接冲向了疫情现场,那么多人捐钱捐物,善心大发——群体性、全民性的体现出了善。
徽派:关键是这种善与牺牲,更多的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所以越发“英雄主义”。
许春樵:善的升华,就是崇高感。崇高感是超越了善良、悲悯、仁慈之后的拯救、奉献和牺牲精神,与英雄情结相关,是潜伏在人性深处的一种本能,所以,我们时常看到那些特别勇敢的英雄,在救人、救火、保护他人时,义无反顾、慷慨赴死,都是没经过大脑考虑,是没有理智分析的,没有理智的冲动就是本能的反应。有上海进修的武汉的医生,在封城后历经千辛万苦赶回武汉抗疫病房的,还有那个渐冻症的院长,还有骑几天自行车回到武汉岗位的女护士,很多。不像古希腊有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和战神阿克琉斯,和平年代的英雄是缺席的,医患关系一直很紧张的医护人员,现在都成了英雄,没有人吃回扣,没有人收红包,没有人乱开药,这就是人性的善被还原,崇高感被激活。这也是疫情带给我们的人性的变化。
E 不能把作家定位为记者和宣传干部
 徽派直播中
徽派直播中
徽派:在家会用文字记录疫情么?您说的手头在创作的长篇是什么主题?
许春樵:记录疫情没有。写长篇很辛苦,必须专注地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要混成朋友,成为亲人,才能写出有品质的作品。写长篇需要写作状态,去年事务太多,活动太多,一直没有成块的时间进入长篇写作,这次疫情也是我写作的一次机缘巧合。
手头的这部长篇,是现实题材,情感主题,是关注精神、情感和心灵,而不是关注现实事件本身。当下整个中国社会在转型,经济上的产业结构转型,观念中的精神结构转型。过去整个社会都在追求外在的东西,追求物质生存,房子、车子、票子,是每个人没法回避和必须努力争取的生活目标,40年改革开放基本解决了这些基本的物质生存问题,那我们还要解决什么,这就是精神问题、情感问题、心灵问题,这就是精神结构中的由外向内的转型。以前作家强烈干预、质疑甚至批判现实,和现实纠缠得太紧,而现在应该关注现实事件背后人的情感与心灵的迷茫、困顿、挣扎,以及对灵魂出路的寻找。由外向内,社会精神结构的转型成为了当下的时代主题,那么多焦虑症、抑郁症患者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我们的左右,他们不是缺少粮食和水,缺少房子与车子,而是缺少情感的安全、精神的自足,灵魂的关怀。以前我们上大学,强调的是哪个专业好,能挣钱,能给娘老子带来荣光,但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大学生内在的需求,内心里喜欢什么专业——当年高考我叔叔让我上财经大学,说毕业后分到财政局,吃香的喝辣的,我说我不喜欢跟账本子打交道。
徽派:嗯,您很幸运,坚持了自己内心的选择。
许春樵:现在的90后00后已经开始转型,他们注重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和体验,以前大家说你在报社上班,是记者,收入高,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不会顾及你内心里真正喜欢什么,愿意干什么,世俗的价值尺度必须转换成量化的物质数据;我以前创作的《放下武器》、《男人立正》也是对现实的干预,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现在不用这样写了,我们需要从情感心灵出发,感受、发现、体验和判断生活。
这次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许多观念。改变观念比改变生活更加重要。
徽派:这样一个重大事件自然有各种发声,作家们也在选择用日记、诗歌等文学形式去记录去表达,但也遭受了大量的质疑,您怎么看?
许春樵:我看了很多疫情期间的作家文字,也看到了许多议论。隔行如隔山,许多非议没法交流,也不需要交流。作家关注什么,作家的作品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这是一个专业问题。作家的作品不是新闻,不是宣传材料,不能把作家定位成记者或者宣传干部。比如方方的日记,是一种灾难下作家的情感体验和精神记录,体现出的是作家的悲悯情怀恻隐之心仁爱之心,笔下更多的是受难、挣扎和疼痛,这与新闻和宣传的记者是不一样的,他们要宣传报道人们众志成城向病毒宣战和抗击病毒。其实这是各司其职的定位,作家、记者、宣传材料从不同角度全方位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应该说缺一不可。关于作家记录灾难中的不幸与受伤,这与文学的职能相关,文学的视角、对象、价值是有特定的专业规定性的。比如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悲剧史,怎么理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悲剧快感,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分析出悲剧是具有审美力量的,是打动人心感染人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日本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卡夫卡说写作是为了缓和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足见文学是给人安慰、给心灵疗伤,让情感共鸣的,悲剧就是承担了释放和缓冲内心痛苦与压抑的功能。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到中国的《红楼梦》《孔雀东南飞》、《雷雨》、到琼瑶小说电视剧,都是悲剧审美,这几乎就是文学常识。文学写悲剧,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恰恰是为了警醒人们如何逃离悲剧,写灾难是为了避免灾难,写死亡是为了珍惜生命,不是宣扬灾难和模仿死亡。你看完电影《泰坦尼克号》走出电影院泪流满面,但你内心里是舒服愉悦的,这就是悲剧快感,而且你会从这出悲剧中懂得了珍惜生命和缘分。假大空的东西不走心啊,不能打动人。李清照和柳永的词,为什么能打动你?写的都是失恋。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如果都上岸了,男女主人公在教堂结婚,又生了个胖儿子,那就不是艺术品的《泰坦尼克号》了。
徽派: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
许春樵: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不是建筑工程师,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搞错了。你这作家阴暗,怎么都写阴暗面呢,作家写人生苦难和不如意,出于内心的善良、仁慈、悲悯,作家不愿看到众生受苦,不愿看到心灵受伤,于是就代人受过,为人赴难,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而作品中的生活与作家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作家的人文情怀就在这里。文学的呈现方式和新闻宣传不一样,但总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歌颂至真至善至美,鞭挞虚假罪恶丑陋,让社会走向健康和美好。
徽派:看来许老师疫情期间笔没停,思考也一直没停。
许春樵:我都会关注。还有,感恩,也是很好的素材。给援助医生送行,鞠躬的、跪下的、警车开道的欢送仪式,都是人性善和美的表达。这是新闻题材,也是文学题材,但怎么做?文学有文学的手段和视角,感染人、打动人心,期望所有人都走向善良,唤起人的同情心悲悯心恻隐心,这是文学的使命,不能像汶川地震时的那个诗人,为了歌颂举国救灾的伟大,让死人在坟前看奥运,还和活人一起欢呼,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这不仅不善,而且灭绝人性,这是作家作为一个人的最大的悲剧。
徽派:聊过之后还蛮期待,许老师以后可以能有一些文学性的表达。
许春樵:可能会有。疫情题材有大量作品可以写,不排除以后有机会写这方面的题材。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 蒋楠楠/文 薛重廉/图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