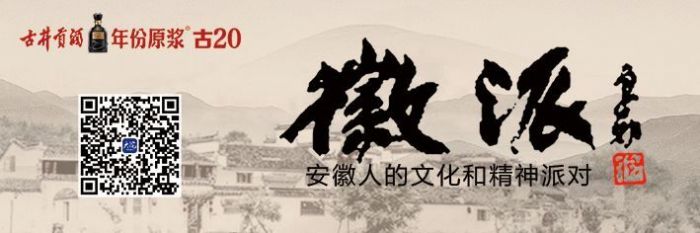
访谈视频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 15日下午,曾执导《中国文房四宝》、《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纪录片导演吴斯做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的大皖徽派栏目。1月7日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年首,一部全景式展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以安徽金寨县59位开国将军为主体人物的大型纪录片《八月桂花遍地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和安徽卫视先后开播,央视频、学习强国、哔哩哔哩、西瓜视频等平台也跟进播出,收获上佳口碑。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便是吴斯。
抢救性拍摄詹大南少将
微动一动手指感慨万千
 导演吴斯
导演吴斯
徽派:《八月桂花遍地开》在央视纪录片频道刚刚落幕,有收到印象深刻的反馈吗?
吴斯:节目播出期间,微博话题#八月桂花遍地开# 阅读量突破5000万,金寨59位开国将军的后代,红二代和红三代,他们非常感动,在群里给我们留言,从来没有如此全面的反映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历程的完整纪录片,包括101岁的万海峰上将,他不是我们安徽人,但是他跟我们的这些将军们一起扛过枪,我们特别通知了万老收看,他的秘书说301医院的病房看不到央视纪录频道,他们就想办法,在电脑跟前看,万老看得非常认真,令我们感动。包括去年去世的我们安徽省最后一位开国将军詹大南少将,他原来是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他去世时是105岁,我们通知了詹将军的女儿詹化文老师,詹老师说和家人每晚都准时收看,希望节目组制作一些光盘,我们就说尽快制作,一定送到你们手里。另外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很多年轻的观众喜欢,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有大学生留言说,要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做到有信仰、有追求、有行动,实现价值。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在于此。
徽派:听到这些肯定很开心,这是纪录片的力量。
吴斯:对,我们团队还是很兴奋的。
徽派:这不是你们团队第一次做这种题材了吧?
吴斯:之前有过,过去可能是单个人物,这次是大体量的重磅嘉宾,群像式反映,以金寨县为原点,反映鄂豫皖根据地,反映大别山地区,这个应该在全国来说也不多见。
 《八月桂花遍地开》剧照
《八月桂花遍地开》剧照
徽派:大量的人物需要寻访,主要的困难在哪里?
吴斯:一开始台领导就定下来,我们和金寨合作。开始我是计划从中抽取一二十位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做6集,这样从容一些。但是领导要求,59位开国将军一个都不能少,这个就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立项的时候,58位将军都已经去世了。在世的就剩詹大南将军,而且他当时已经在病床上不能说话。我们马上就进行了一些抢救性拍摄,这些将军的第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南京。詹大南将军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全家人省吃俭用,捐助了金寨的希望小学,我就设计,通过希望小学校长,带两个学生,去南京看望詹将军。他的意识忽有忽无,家人照顾很好,当他女儿詹化文老师在他耳边说“爸爸,咱们老家杨桥小学的代表,来看望您来了”,我听到那个声音其实也挺感动的,因为詹化文老师也70多岁了。詹将军听完手指动了一下。包括一些金寨籍、六安籍的老红军,我们都进行了一些抢救性拍摄。
追溯历史从当下现实入手
重返过去让参与变成洗礼
 海报
海报
徽派:很多将军已经不在了,怎么做纪实性的还原和叙述?
吴斯:我们进行了一些抢救性的拍摄,去世了怎么办?我们在对他们的后代采访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说,老人家很少和我们讲这些事情。真的很难。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后代,说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故事。我说为什么呢?说他们很知足了,多少战友牺牲在战场上,自己从一次次战斗中活下来,能够活到新中国,过上这样的生活,很知足了。
徽派:所以他们选择不把那些苦难的记忆传达给后代。
吴斯:是的,不说,也很少写,我们掌握的资料非常少。我们看很多国外的片子,士兵会写日记,但是我们纪录片的主角,来自大别山的将军,一大批是农民过来,文化底子比较薄弱,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他们觉得不要说,他们已经很幸运了,活下来了。
徽派:朴实且伟大的一群人。
吴斯:对。我们翻阅各种资料,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写得非常详实,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脉络特别清晰,真实度特别高,我们以这本书,包括《金寨红军史》这些文字中去寻找,看有哪些可以挖掘的素材。
徽派:前期准备特别复杂。
吴斯:对,一个是通过大量调研,一个是充分的案头工作。
徽派:准备工作有了,接下来纪实性的故事怎么才能讲好又是挑战了吧?
吴斯:六集体量300分钟,时间跨度很大,从建党之初到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抗美援朝,最后结束是在1955年的第一次授衔。这么大的跨度,将军们的故事是发生在过去。怎么做好历史的故事,吸引当下的观众?从当下现实入手,通过寻访的手段,譬如红二代、红三代,有一些党史军史的研究者,中学思政课老师,作家、画家、演员和军迷,不同人物以不同身份,带着各自的任务进入,就会特别身临其境,就是从这里渡河的吗?吃的就是这个野菜吗?就是这个战壕?就是从这里降落的吗?有些地方还在大山里,有些地方变成了学校,有些地方变成熙熙攘攘的街道,把观众代入历史发生地。
 寻访摄制中(资料图)
寻访摄制中(资料图)
徽派:这些寻访者和我们的红色故里有渊源么?
吴斯:首先是感兴趣的人,另外,他们有不同的任务,比如演员王雅捷,当时她正在准备一个红色题材的作品,她的父亲王和泉老师是《再见了,大别山》的词作者,他带着女儿去寻访,我们觉得特别好。包括一个年轻的作家带着出书的任务去的,每个人跟这段历史都有关联。
徽派:有他们好奇的部分,追根溯源的部分。那这个经历,让他们自身发生变化了吗?
吴斯:前几天我们见到了李业坤老师,他跟我们第三集的导演张魁去了红四方面军战斗的线路,最苦的线路,最后实在受不了了,翻山越岭、悬崖峭壁,他说吴导,我去之前还是做了功课的,我作为一个党史研究者,没想到那趟下来有很多意外收获,收获非常大,再苦再难还是值得的。
强调电视化的表现手法
用声音重塑将军们性格
 吴斯在徽派讲述纪录背后的故事徽派:通过他们的视角也看到你们的不容易。您拍了很多纪录片也获了很多奖,关于纪录片真实性和故事性,你如何融合和平衡?
吴斯在徽派讲述纪录背后的故事徽派:通过他们的视角也看到你们的不容易。您拍了很多纪录片也获了很多奖,关于纪录片真实性和故事性,你如何融合和平衡?
吴斯:我做这个节目,最强调的是电视化的表现手法。我们不是党史军史研究者,不要沉浸在材料中,充分运用电视化手段表现,不要走偏了。观众接受你,接受你要展示的故事。整个节目的结构和布局,59位将军之外,还有和金寨革命相关联的人物。我们金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蒋光慈,是从俄罗斯开始讲述的。蒋光慈和刘少奇、任弼时一起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我们找到蒋光慈的档案。我们邀请了一位俄罗斯著名的研究者,他会中文,给我们沟通带来了极大方便——老师和同学对蒋光慈的评价,他的俄罗斯名字是什么,非常详实,这些资料很多蒋光慈研究者估计都没有看过,包括他同学给他的信、照片,学了哪些科目,都非常详实。比较戏剧化的是,蒋光慈小学有位老师詹谷堂,是进步教师,影响了蒋光慈的人生路。蒋光慈从俄罗斯回来,又影响了老师詹谷堂走上革命路,这是师生间的佳话。还有,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也是在詹谷堂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蒋光慈1926年出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是当时的超级畅销书,国民党当局的“禁书”,再版了18次,影响了胡耀邦、习仲勋、陶铸等领导人,这个怎么能放掉呢?所以实际上这部纪录片的主体人物有80多位,后来我们采取打包方式,经历过同一次战斗的(打包到一起),群像式的,朋友圈一样。重大节点不放过,搜集群像式小故事,6集梳理完了,每一集的人数是不均匀分配的,与每一集的主题相关。
 纪录片拍摄现场
纪录片拍摄现场
徽派:这个统筹和工作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吴斯:第三集讲红四方面军,聚集了20多位将军。我们的分集导演一开始头大,克服重重困难做下来。
徽派:大的框架搭起来,有主有次。
吴斯:对,这样观众印象深刻。电视是画面和声音相结合的艺术,我的考虑是,没有将军们的第一手视频资料,我想到用广播剧的方式,用声音进入,塑造将军的形象和性格。翻阅了很多将军的自传和别人写他们的书,用配音演员,都是给译制片影视剧配音的,观众看画面的同时,通过声音的塑造来想象将军的个性和人物特点,声音的介入是我们新的尝试。
女性导演不想正面战场
小切口妙角度直指人心

詹大南将军女儿詹化文给吴斯看老照片
徽派:框架和形式有了,如何传递情绪情感的部分,作为女性导演是不是更有优势?
吴斯:宏大的题材,主要的气质是阳刚气,但是大的格局下,我们要体现女性导演的优势,挖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亲情、友情、爱情、军民鱼水情,是我们要特别捕捉的,能更好地打动观众。第五集,红二十八军坚守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从我们得到的反馈看,大家都get到了那几个动情点。
徽派:你有自己拍摄的初心?
吴斯:我们不想正面表现战争,从电视包括电影的表现方式,正面战争,我是女性我不关心这个,我关心战争背后的故事,战争前五分钟,生死抉择时的胆怯和犹疑,好多东西不能从正面攻。所以我们是小切口和巧妙的角度。
徽派:你有说过想把这部片子打造成有声有色的面对年轻人的思政纪录片,怎么理解?
吴斯:思政课很重要,特别对学生来说。学生不愿意接受硬邦邦的教育,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将士们的故事,让他们感受那个年代先辈的付出和贡献,感受到现在的和平来之不易,历史、现实、未来,通过我们的方式让更多年轻的观众感受到,纪录片式的思政课。
 剧照
剧照
徽派:除了配音还有什么特别的“声音”?
吴斯:原创音乐,这次是非常成功的。两位作曲,谢国华老师和他的学生徐兴民,谢老师80多岁,他的专业和敬业,让我们非常感动。起初我们考虑人选的时候没有想到谢老师,从北京到上海到南京,没有发现特别合适的,后来和南京特别出名的录音师陈小东老师联系,他就问你有没有考虑谢国华老师,我说我做《严凤英》时就是和他合作,我说他还在创作么?他说当然了,经常给我发国外影视音乐。谢老师有交响乐的基础,对大别山又特别了解,80年代创作了一部舞剧《冬兰》,就是大别山题材,他探寻我们的主题,我们想要达到的精神层面,人物脉络,都会了解一清二楚,特别严谨认真。我给他的时间很有限,最初的灵感来自我跟他说的俄罗斯的故事,隔着电话用钢琴弹给我听,我说太棒了,我要国际范儿,也要民族特色,特别准确。谢老师擅长用竹笛,大别山特别适合用竹笛,一下子抓到片子的气质,几段主旋律写得特别好,我非常满意。
徽派:他的音乐思维是偏传统的吗?
吴斯:没有老观念、老思想。我们是用交响乐队演奏的,有明亮的、抒情的、低沉的、急促的,有大提琴段落、小提琴段落、手风琴、口琴,草地夜行的时候用了一段口琴,音乐是不同的调性,我们的故事也要起承转合,悲壮的、抒情的、肃杀的,不同的情绪在一起。
绘声之外还有专业绘色
艰难困苦中显伟大人性
 创作团队
创作团队
徽派:“色”这一块有哪些亮点呢?
吴斯:之前《中国文房四宝》是我们省第一部4K纪录片,那个磨合之后,这部片子摄像团队还是同一个北京团队的。总摄影徐欣,是一个非常职业的摄影师,完全是投入的,敬业精神是很好的。咱们片子非常苦,非常艰险,第三集拍长征,一圈下来,他们整个团队有一次去了30多天,从安徽到四川、云南、甘肃很多个点,徐欣牙齿发炎天天吃不了饭,研究镜头怎么捕捉和表现,始终和导演在沟通。摄像团队是非常成熟的团队。包括我们的航拍团队,贺孝山应该是安徽最好的航拍摄影,前几天我儿子抽空看了第三集、第四集,看到河南伏牛山,白雪皑皑的的航拍画面,他说妈妈你们这个镜头可以和张艺谋媲美,我说你这个评价特别高。航拍不仅是俯瞰,很多贴近人物和环境,中景、小全的景别,画面叙事性特别强,也是加分的,功不可没。
徽派:以前不少纪录片导演来过徽派,经常听到很辛苦的一面,理念的融合,大家都要争半天,你这方面有没有优势?
吴斯:我们这个团队,老弱新,是这么个组合,我们开始参与调研的导演以女性为主,都是女汉子。有导演怀孕,不能继续,另外一位部门调整,一位退休,都没有留在这个项目,中间有青黄不接,后面陆续进来几位导演,听说我们做这样的题材,有导演就退了,但是这几位导演,韩德良、丁晓明都是知难而上,都是超过五十岁的人。老同志不怕艰难上,我们是老中青结合。从栏目、从新闻转型纪录片,两位分集导演都是第一次。还有一位张俊楠导演从来没有做过节目,我说我有点后怕,因为她当时主动要求想做,跟我要求很多次,我说带着你尝试一下。一开始完全不懂镜头,不懂怎么创作,三年下来,把节目能攒起来。自己的历练和大家的帮助,离不开各位老师给她的帮助,一个小白被磨炼起来。其实挺危险的,以后不能这么做。我担心如果片子成功了她会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进步空间还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她被这种操作压垮了,从此一蹶不振。但是团队确实青黄不接了,没有办法。熬下来,是很大的收获。
 海报
海报
徽派:熬下来就有收获。你看成片时有什么感受?
吴斯:应该是这样的,片子首先要感动自己,才有可能感动别人。有几个故事,我每次看都会有眼睛一热的感觉。拍摄过程中我们到了很多红军的墓园,你看一座座墓碑,很多没有名字的,给我们触动非常大的。四川通江王坪一个红军烈士陵园,1934年红军自己给战友建的,现在两万多烈士安葬在那里,一万多无名烈士。各种各样规模的,山窝窝里的,非常简陋的,都有。实际上,你看看那些埋葬在那里的人,震撼非常之大。他们也都是年轻娃娃,也就一二十岁,回不到家乡,看不到解放。我们受到很大震撼。我们看似是在表现59位将军,实际上我们在说10万金寨儿女,在说鄂豫皖,在说大别山人,在说他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这部片子给我们创作者触动,通过我们的故事,让当下的年轻人受到感染,启发他们更进一步的行动。除了央视纪录和安徽卫视,我们小屏上也都有播放,学习强国和B站,我们就是想让更多年轻观众看到,受到感染和启迪,希望红色基因能够有所传承。
徽派:刚刚提到你儿子,无论B站的年轻人还是你儿子,你会怎么安利《八月桂花遍地开》?
吴斯:我儿子也是我的忠实观众,现在高二,之前那部《中国文房四宝》,播出之前他已看了很多遍。这次他抽空看了第三集、第四集,一边看一边评论。他喜欢音乐和解说的声音,还有对地图感兴趣,说你们地图做得帅,能感受到革命前辈从敌人重重包围之下穿出来,突出重围,非常艰难,非常了不起。我们另外一位导演鲁慧的孩子,小学生,每天按时在央视纪录频道追着看。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徽派:真好,看来你的初心和使命也算达成了,这是当代最挑剔的一批观众,也是他们最需要的。让他们看到艰难困苦中的坚定信仰和忠诚情怀。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 蒋楠楠/文 薛重廉/图






请输入验证码